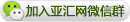药品受试者的江湖
在新药上市前的一系列程序中,通过人体试验是必要且关键的环节。但对一些药品受试者而言,这更像是一种交易,甚至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汲东野
王飞看上去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当在约定的地点看到法治周末记者的时候,他飞快地从自行车上跳下,说了句:“你好!”
作为一个在试药这个圈子里浸淫已久的“老人”,王飞是为数不多的愿意直面媒体的药品受试者之一。在这个圈子当中的大多数人,更愿意把自己藏得深深的,而不是暴露在聚光灯下,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试药,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王飞却不这么认为:“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其中的社会价值,这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不过,王飞也不否认,在药品受试者这个群体当中,大部分都是为钱而来。很多人甚至压根都没有考虑过其中潜在的风险。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只需要在医院吞下药片或者接受注射,然后就可以拿走或多或少的补偿费用。
这是一门来钱快的生意,只要你有一副合格的身体,不需要什么技能,也不需要什么学历,更不限户口,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参与。
低门槛的生意迅速网罗了一批贴着外地人、没学历、缺钱花、“蚁族”等标签的年轻人——而他们大多是怀着梦想而来。
老“药人”的经验
苏素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18岁的苏素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时,正值2008年,此时的他和这座雄心勃勃的城市一样试图一展满腔的抱负。这一年,不论是对于北京还是苏素来说,都是最迷人的时刻。
不过,迷人的时刻转瞬即逝,赚大钱的目标也渐渐远去。在北京摸爬滚打了4年之后,苏素彻底失业了。
2011年6月的一天,似乎注定要成为苏素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失业两个多月的苏素在交完数额可观的房租之后捉襟见肘,而即将到来的生日则让爱面子的他更加焦虑不安。就在此时,他想到了一个很久前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 一个药品受试者。
最终,这个源于网络的朋友不仅带给苏素一份解决燃眉之急的工作,更把他带入了一个新的圈子,在这个圈子中,就有王飞和李力。
和北漂苏素不同,王飞是圈子里为数不多的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着让大多数试药者羡慕的家境和学历。不过,这并不妨碍王飞和苏素有一个相似的入行经历。
同样是失去工作,同样是没有积蓄,同样是和朋友聚会需要大把的花销,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自尊心很强的王飞不愿开口向家人要钱。
“之前上中学时就在电视上知道药品实验。当然,做这个之前,跟别人一样,我也会担心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我都会去做调查。而且不只是查药品本身,还会查一些圈子里的黑幕,包括一些潜规则的东西。”王飞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理工科出身的王飞很快就把他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并掌握了很多圈子里的一手资料。
比如:北京和上海是国内试药行业的两个重镇。和北京相比,上海的药物试验会比较少,但是上海医院的试药技术比较高,给的钱也多,不过危险性也偏大。
再比如:北京的药品受试者大多来自北京周边。“像河北涿州、保定、石家庄的比较多,再往外就是山西、山东和辽宁,不过就会相对少一些;其他地方就是极个别的了。”
而对于药品安全性的调查,王飞也认为自己做的比别人要更全面。
“我一般不去看医药广告,可能会在网上查一些学术期刊,包括类似的药在之前做过的试验,也会在圈子里打听一下口碑怎么样。”按王飞自己的话说,“就是把风险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
苏素也是药品受试者中比较谨慎的一个。苏素坦承,第一次试药时,他很害怕,担心药品的安全性。
好在苏菲一开始就碰上了好人。有“老人”告诉他,试药要选危险性低的药,比如像消炎药、疫苗等。因为这些健康人用起来就问题不大的药,一般来说对身体的伤害应该也要低一些。苏素说,这些经验让他很受用。
不过,更多的职业药品受试者在试药前并不会想太多,对他们来说,能试药拿到钱就好。
27岁的刘东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刘东来说,他最担心的不是药物本身所潜藏的风险,而是过不了体检。所以,几乎每次试药之前刘东都会对自己的身体格外仔细。
“不熬夜、不喝酒。不然容易出现转氨酶高,白细胞量不正常等问题。”刘东很乐于跟记者分享自己的经验。
走样的人体受试
据王飞介绍,在药品测试正式开始之前,医院会进行一次体检,体检合格才能真正进入测试。体检的项目通常有量体重、身高、血常规、血生化、心电图、尿常规、胸片等,药物滥用、药物上瘾等也都是必查项目,个别还要进行酒精测试、抽烟测试等。
刘东所担心的就是这个体检。但事实上,职业药品受试者们在应付包括体检在内药品测试程序上往往有自己的一套“绝招”,像不熬夜、不喝酒只能算做常识。
“比如,一般医院规定试验前3个月内做过其他试验的受试者不能接受别的试验。但是由于医院之间没有联网,所以医院通常也无法知道。倘若真要查针眼,你可以说自己最近做过哪里的检查,但是体检没过。医院也会放你进去。”
苏素告诉记者,自己就曾同时进行过两个试验。
而对于血检、尿检,苏素们也都有相关的解决方法。
比如,用10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如果血液里白细胞较高,那么体检前去献血小板;而尿检,则甚至可以轻易换成别人的样品——提前准备好别人的小瓶尿样,绑在大腿上,这样取样时的温度也不会引起护士的怀疑。
在检查过程中,药品受试者们也会有一些“招数”对自己进行“保护”。比如,吃药时不将药片咽下,等医生走了再把药吐出来。当然,这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因为服药后医生会要求药品受试者张开嘴巴进行检查。
不过,令王飞感到奇怪的是,医院最后所得的检测结果却往往与试验预期相同。“我在医院做了这么多次试验,就知道有一次是数据结果和预期不一样,其他试验都是成功的。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受试者都是吃了药,当着大夫喝口水,回头就给吐了,实际上都没吃。”
说到这里,王飞夸张地睁大双眼,用戏谑的口吻继续说:“这样如果说能得出正常的数据,这里面的数据……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出来的。没吃还能得出所期待的数据,这是很神奇的事。”
事实上,王飞就不止一次地发现,试验结束后的最后体检和第一次体检的规格就完全不同。“项目还是那些项目,检查结果该怎么弄就怎么弄。”王飞告诉记者,因为如果出现问题,影响试验结果,药厂不希望看到,医院也不希望看到。
“比如容易处理的结果,血液里的某指标高了,兑点蒸馏水,指标不就下去了么。简单的处理无伤大雅,基本上对你的身体没有极其严重的原则性问题,就给你处理了,就是把你的体检结果做合格了。因为你毕竟不是病人。”王飞说。
试药者的风险
不过,钱并不是像看上去那么好拿。既然是试验,总归隐含着风险,而这些风险一旦显现,则不会像试验结果那么容易处理。
李力就很不幸。
这个来自山东农村的年轻人第一次试药很顺利,那是一种消炎药。在服用之后,李力身上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感觉。这次受试不仅帮助李力解决了三天的住宿问题,还让他的手里多了2500元的补偿费。
第二次试药,补偿费1万元。面对“极其可观”的报酬,第一次成功之后的李力彻底放松了警惕,甚至都没有看清等待他的是什么药物。他兴奋地体检、等待,在签过《知情同意书》后,护士在他的小腹扎了细细的一针。
他想不到,这一次的试药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后半生。
这是一次抗肿瘤药物的试验,和其他受试者一样,随后他开始感觉口渴、心慌。但是当其他人在两小时内都恢复了正常后,他依然心慌难受。
“心率已经降到40次,心电图的数据完全不正常了,医生跟我说是心律不齐。”李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最终医生也没有找出原因所在,建议他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于是,尽管3针的药只打了一针,李力还是拿着1万元回家了。
然而,在此后的日子里,李力一直出现心律不齐、胸闷的症状。即便是两年后的今天还是常有胸闷的感觉。
李力告诉记者,在这此测试之后,他再三联系当时负责的医生,就再也没有得到回应。“我给他们打电话、发短信,他们一直都不理我。”李力感到很无助。
“知情同意书中写的是有病管治,一直到治好,如果出现这种不可逆的损伤,比如治不好的不可逆的损伤会给钱,给补偿。但据我了解,一期临床试验,有很多出过事儿的,没有一个维权成功的,三期临床试验有维权成功的。”王飞告诉记者。
据王飞介绍,一期临床试验受试者是健康人,主要测三个项目,药物代谢、药物等效、药物耐受这三个项目;二期是做药效;三期是测药量,看吃多少合适。李力做的就是一期临床试验。
直到5月24日,李力给医生发去一条短信,表达了“近期有媒体采访了我,我只想把病治好,并不想要多少赔偿金”的意思。在发去短信的第二天,李力收到了回复,对方表示医院开始处理这件事,此时李力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事实上,两年来李力一直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件事。
他告诉记者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自己对法律不熟悉;另外一个则是因为自己的《知情同意书》丢了——他一直以为自己手上没有证据。直到近期有律师告诉他,医院也是有义务为患者提供合同的副本时,他才知道,此时诉诸法律也是可行的。
“我也许不应该给他发那条短信的。”李力对记者说。
被忽视的《知情同意书》
李力的情况在这个群体的维权者中很有代表性——大多数的维权者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而最终成功拿到赔偿的则少之又少。
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可见一斑。
据王飞介绍,在进行测试之前,医生会先向受试者介绍试验的药品、基本流程、药品会产生的不良反应等。如果受试者没有问题的话,就开始签署《知情同意书》。但是,在很多受试者看来《知情同意书》只是几张写满字的纸。
“有些人可能都不会拿,还有些人出门就扔了。”王飞告诉记者。
事实上,《知情同意书》是药品受试者的主要保护途径,受试者所应当享受的权利都被印在这份文件当中。
比如,在法治周末记者拿到的几份《知情同意书》中,在“不良事件”或“发生研究相关损害时对受试者的赔偿和/或治疗”标题下,都可以见到“申办者对参加临床研究的受试者提供了保险,对于发生与试验相关损害的受试者承担治疗费用及相应的经济补偿”的字样。
不过,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多数的《知情同意书》并没有给受试者带来足够的保障。王飞就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在自己做过的十多个测试当中,没有一个跟他提及或办理保险。
而根据我国已经颁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第四十三条规定:“申办者应对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提供保险,对于发生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或死亡的受试者承担治疗的费用及相应的经济补偿。”
但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丛亚丽看来,该规范没有具体的补偿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差。这导致很多受试者拿不到补偿。
“目前对于职业药品受试者几乎没有任何的法规和政策的监管和保护,我国只有较大规模的医学院校、研究机构和三甲医院,才设置专门的伦理委员会。”丛亚丽说。
丛亚丽所说的伦理委员会是专门核查临床试验方案,确保受试者权益的独立组织。
按照规定,临床试验开始之前,研究组须提前向所在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包括研究方法、目的、受试者人数等,甚至试验的每一步都必须进行详细计划。只有伦理委员会同意研究方案之后,临床试验才可以正式进行。
“但是,伦理委员会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一些伦理委员会虽然会对提交的书面内容进行审查,也会询问试验人群的来源等,但可以想象,对于此类人群的入组,难以通过此委员会来禁止。只有较少的伦理委员能够坚持持续审查一年时间。”丛亚丽说。
不过,受试者们已经迎来了曙光。
就在4月1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书面复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表示将根据法院提出的司法建议,适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明确临床试验中申办者在试验实施前对受试者保险措施的要求;同时,强化伦理委员会的职责,加强对受试者保险措施的审查,最大限度地保护受试者的权益和安全。
这对试药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不透明的受试者补偿
事实上,这些保障对于这些大多徘徊于城市边缘的受试者极其重要。
在受试者扎堆的QQ群中,随便点开一个群成员的个人资料,就可以看到写着“自由职业者”的个人介绍。而在这些以“受试者”、“临床实验”等关键词命名的群中,除了受试者招募的信息之外,还不乏各种兼职——甚至卖血的小广告。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试药群成员告诉记者,在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要是不缺钱谁干这个”?
过,几乎所有的受试者都会遭遇克扣补偿费的情况。王飞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这个圈子中,受试者的地位很低,被扣钱的情况很严重。
“大头是医院扣的,剩下的中介扣一部分。到受试者手里,钱已经没有多少了。”王飞告诉记者,“比如去年一家三甲医院的试验,药厂给的价钱是每个人9000元;从医院项目负责人到中介,变成6000元;然后中介再拿走2000元,到受试者手里就只剩下4000元了。”
而据多个受试者介绍,目前药品受试者的招募主要是由中介垄断的。
“通常一个中介会包下一家医院或者两三家医院的受试者招募事宜。”苏素告诉记者,中介会和医院直接接触,而受试者的补偿金也由中介来给。
“我们不知道医院到底给中介多少钱。但是,中介在收了医院给的招募费之后,再从给我们的钱中提成,就不合适了。”苏素说。
如果说克扣补偿费的事情让王飞愤愤不平,那么作为受试者所遭受的歧视则让他难以接受。
“事实上,不仅仅是试药者,从事临床试药的大夫以及招募人都希望得到社会的正视。但是这个行业本身太不干净,自己都不把自己洗干净,怎么让社会积极的看待他。”王飞认为,一方面医院希望社会正视“试药”,但另一方面却没有给受试者足够的尊严。
“有的医院就认为受试者是为了钱才去的,把受试者看成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认为是没有必要被尊重的,或者完全把受试者当小白鼠。”王飞说。
王飞回忆,有一次中午发盒饭的时候,一个试药者嘟囔一句:今天怎么又吃鱼……大夫就写上这人对鱼过敏,以后都不能来试验。“去试药的人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一个试药的机会对他们来讲非常宝贵。”
因此,如今已有不少职业试药者开始脱离这个曾经带给他帮助或者伤害的圈子。
李力就找了一份月薪三千多元的工作——修电梯,他已经彻底放弃试药了。“因为要养家,在北京一个月3000元的收入,生活还是会比较拮据。前段日子,我报了一个培训班,希望以后每个月能拿到1万元左右,那样未来就没有问题了。”
苏素也在完成了第6次试药后,下定决心再也不做试药了。“毕竟是药三分毒,不管试什么药,通过肝吸收之后对身体影响都挺大的。况且赚到的钱太少,刚好只能够生活所用,根本攒不下来。”所幸,他的身体并未因此而感觉到不妥。
苏素说自己有时也会和曾经一起试药的同伴联系,“他们有的比我做的时间长得多,现在全都上班了。有的在做电话销售,有的在做机械维修。我之前也会跟他们说,咱们有空还是踏踏实实上班吧,老做这个不行”。
不过,王飞依然不打算放弃试药,虽然他也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个东西不能少,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说到这,王飞停顿了一下,眼神里面忧郁了下来,“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之前没有跟别人提,我家刚刚发生了一件事。4月16日,我母亲去世了。”